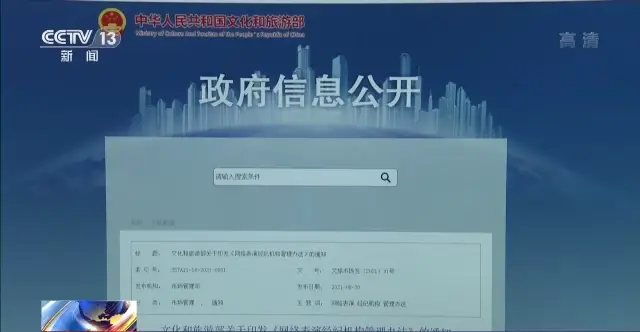
在互联网平台刷赞操作是否构成违法问题,已成为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法律议题。随着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的深度渗透,刷赞行为从个人自发行为演变为产业化运作,其背后涉及的法律边界、市场秩序与平台生态的复杂性日益凸显。要准确判定刷赞的违法性,需穿透技术表象,从行为本质、法律适用、社会危害等多维度展开分析,而非简单以“是”或“否”二元化定论。
刷赞行为的本质,是通过非正当手段人为制造虚假流量,扭曲互联网平台的评价体系。从操作模式看,既有个体为博关注进行的“自我美化”,也有商家为提升销量组织的“流量造假”,甚至形成涵盖“刷手中介”“技术工具”“账号资源”的黑色产业链。其核心特征在于“虚假性”——通过机器批量点击、人工模拟点击、数据接口篡改等方式,虚构用户真实反馈,使平台算法或公众认知产生误判。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互联网平台“真实、透明”的基本运行逻辑,与平台设计的“用户评价—内容分发—商业变现”机制形成根本性冲突。
从法律层面审视,刷赞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需结合具体场景与危害后果,援引不同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判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刷赞行为若由经营者实施,例如电商商家通过刷单刷赞提升商品评分,或MCN机构为网红伪造粉丝互动数据,本质上属于“虚假宣传”或“商业诋毁”,通过虚构商品或服务质量误导消费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近年已有多起处罚案例:某化妆品企业因组织刷单刷赞,被处以罚款及吊销营业执照;某直播MCN因伪造点赞数据,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承担赔偿责任。这些案例表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刷赞行为,已构成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具备明确的违法性。
若将视角扩展至非商业场景,个人刷赞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则需审慎区分。例如,用户为朋友朋友圈内容点赞、为偶像微博刷赞等行为,若仅限于少量、零星的个人自发行为,且未对平台秩序或他人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通常难以纳入违法范畴。但若形成规模化、组织化的刷赞团伙,例如通过“兼职刷赞”平台招募用户,以金钱激励为诱饵进行大规模虚假点击,即使不以直接营利为目的,也可能因“破坏网络生态秩序”违反《网络安全法》或《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此外,若刷赞行为涉及数据造假,例如通过技术手段绕过平台反作弊系统,非法获取用户账号信息或篡改后台数据,则可能触犯《刑法》中“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面临刑事责任。
互联网平台在刷赞违法性认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平台生态的管理者,平台通过用户协议、社区规则等明确禁止刷赞行为,并采取技术手段(如识别异常点击频率、分析用户行为特征)进行治理。但平台规则的约束力有限,对“隐蔽性刷赞”(如通过境外服务器代理、分布式IP池操作)的监测难度较大。此时,法律需介入填补监管空白:一方面,平台需承担“守门人”责任,建立更完善的流量监测机制与违规惩戒体系,对多次刷赞账号采取限制功能、永久封禁等措施;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推动“平台责任法定化”,明确平台在数据审核、异常流量处置中的法定义务,避免“放任不管”或“过度监管”的两极分化。
当前刷赞违法性认定的难点,还在于技术迭代带来的法律适用滞后性。随着AI换脸、虚拟人、自动化脚本等技术的普及,“真人模拟刷赞”“AI批量互动”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传统“人工计数”“IP地址识别”的监管方式难以应对。例如,某虚拟偶像团队利用AI算法生成虚假点赞数据,其行为是否属于“虚假宣传”,现有法律尚未给出明确界定。这要求立法机关及时更新法律概念,将“人工智能生成数据”纳入规制范围,同时司法机关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新型刷赞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避免出现“法律真空”。
更深层次看,刷赞行为的泛滥折射出数字时代“流量至上”的异化价值观。在“点赞数=影响力”“好评率=销售额”的单一评价体系下,部分用户与经营者将刷赞视为“捷径”,忽视内容质量与服务本质的真实价值。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不仅损害消费者知情权,更导致优质内容被劣质流量淹没,阻碍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治理刷赞行为不能仅依赖法律惩戒,还需构建“技术+法律+行业自律”的综合治理体系:通过算法优化让优质内容获得自然流量倾斜,通过信用惩戒让刷赞者付出代价,通过行业倡导重塑“真实、健康”的数字文化。
归根结底,在互联网平台刷赞操作的违法性问题,核心在于其是否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真实透明的网络生态。商业化的刷赞行为,因具有主观恶意与实质危害,应明确认定为违法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非商业化的个人刷赞,需根据规模、手段及后果进行个案判断,避免“一刀切”扩大化。唯有通过法律规制划定底线、平台治理压实责任、行业自律重塑价值,才能让互联网平台回归“内容为王、真实为本”的初心,让每一个点赞都承载真实的情感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