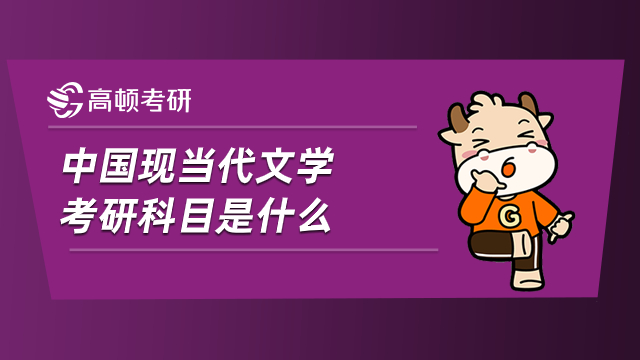
当代校园中,“做连接点赞”与“刷礼物”已从边缘行为演变为渗透学生日常社交、活动参与甚至身份认同的常态化现象。这种看似简单的数字互动,实则折射出数字原生代在社交场域中的深层焦虑、校园生态的技术化重构,以及青少年群体对“可见性”与“价值确认”的极致追求。其本质并非单纯的娱乐行为,而是数字时代社交逻辑在校园场景下的异化与重构,背后交织着技术发展、群体心理、教育引导等多重动因。
数字原生代的社交逻辑重构是现象滋生的土壤。这代学生自出生起便浸泡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点赞”早已超越其原始功能,成为社交货币的具象化符号。在校园这个高度同质化的社群中,学生的社交半径被极大压缩,同学、室友、社团成员构成了核心社交圈,而“点赞互动”成为维持这种弱连接的低成本方式。一条动态下的十个点赞,可能来自不同班级的同学,这种“泛连接”的建立,让学生感受到“被看见”的安全感。与此同时,校园社交中的“同辈压力”被数字工具放大——当某位学生发布的活动照片获得大量点赞时,这种“数据反馈”会转化为隐性社交资本,促使其他学生模仿参与。例如,在班级评优、社团招新等场景中,学生通过“拉票点赞”积累支持度,点赞数直接关联资源获取,使得“做连接点赞”从个人行为异化为群体性竞争策略。
校园社交中的价值异化与群体焦虑,则催生了“刷礼物”现象的蔓延。与点赞的“轻互动”不同,“礼物”在校园场景中往往指向更具价值的实体或虚拟回馈,如直播打赏、班级活动“心意礼”、线上竞赛“助力礼”等。当学生发现“礼物数量”能快速转化为可见的社交地位——比如在校园主播中获得“榜一大哥”的称号,或在集体活动中通过“刷礼物”成为焦点时,这种行为便被赋予了符号意义。更深层看,青少年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在学业压力与同辈比较的双重焦虑下,“礼物互动”成为他们寻求价值确认的捷径。某高校调研显示,超过60%的学生承认曾因“害怕被孤立”而在集体活动中参与“刷礼物”,这种“被动参与”本质上是群体压力下的自我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校园“刷礼物”常与“功利性社交”绑定:学生通过赠送虚拟礼物拉近与“校园红人”的距离,或通过实物礼物交换学习资源、活动机会,使得礼物从情感载体异化为社交工具。
技术渗透与校园场景的数字化迁移,为现象提供了生长土壤。近年来,学校管理、活动组织加速向线上迁移,从“校园APP签到”到“线上投票评选”,从“社团直播招新”到“班级群红包互动”,数字工具已深度嵌入校园生态。这种迁移催生了“数据至上”的评价体系——一场线上活动的参与度、点赞量、礼物数,成为衡量活动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例如,某高校社团联合举办的“校园之星”评选,要求候选人通过直播拉票,最终排名由“点赞数+礼物打赏值”共同决定,直接导致候选人组织粉丝团“刷数据”。技术的便利性降低了参与门槛,学生只需一部手机即可完成“点赞刷礼”的全流程,而算法推荐机制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行为:当校园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热门动态”“礼物榜单”时,学生会不自觉陷入“数据竞赛”的循环,难以自拔。
教育引导的缺失与数字素养的滞后,则加剧了现象的负面影响。当前,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数字社交行为关注不足,缺乏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导致学生难以辨别虚拟社交中的“真实价值”与“数据泡沫”。部分教师甚至将“点赞数”“礼物数”简单等同于“学生活跃度”,在评优评先中予以参考,无形中强化了这种行为的价值。同时,校园心理咨询体系对“数字社交焦虑”的识别滞后,当学生因“点赞数不足”产生自卑,或因“刷礼物”陷入经济压力时,缺乏及时有效的干预。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校园社交平台为追求流量,刻意设计“礼物排行榜”“点赞PK赛”等功能,利用学生的攀比心理刺激消费,形成“平台获利—学生沉迷—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
要破解这一现象,需回归校园社交的本质——真诚连接而非数据竞赛。学校应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理解“点赞”与“礼物”的工具属性,剥离其符号化的社交资本;同时重构校园评价体系,弱化“数据指标”在学生评价中的权重,通过线下读书会、社团实践等真实互动场景,重建学生间的深度连接。唯有如此,才能让校园社交摆脱数字异化,回归到“以人为主体”的教育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