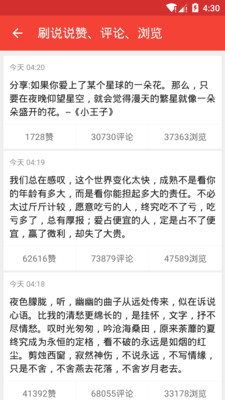
村长谈论科技刷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的今天,这个看似带有技术色彩的短语,实则折射出基层治理与数字化浪潮碰撞出的复杂图景。当村长在村民大会、工作汇报或社交媒体上提及“科技刷赞”,其内涵远不止简单的数据造假,而是涉及乡村宣传逻辑、资源分配机制、基层治理能力乃至数字化伦理的多重命题。要理解这句话的深意,需跳出“刷赞=虚假流量”的刻板印象,进入乡村数字转型的具体语境,剖析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张力。
科技刷赞在乡村场景中的特殊形态,首先表现为“治理工具化”的倾向。 在传统乡村社会,“口碑”是衡量村务工作的重要标尺——谁家路修得好、谁家产业带得活,村民心中有杆秤。但当数字化考核指标下沉到基层,“点赞数”“转发量”逐渐成为新的“数字口碑”,甚至与项目资金、评优资格挂钩。某中部地区村长曾在访谈中坦言:“上面要求我们搞‘数字乡村示范’,要求短视频账号粉丝过万、单条视频点赞破千,可村里会拍视频的年轻人就几个,总不能守着金山喊穷吧?”于是,“科技刷赞”应运而生: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使用“刷量软件”,或组织村民、村干部“人工刷赞”,完成上级下达的数字化任务。这里的“科技”并非尖端技术,而是将现有数字工具(如社交媒体平台、数据接口)异化为应对考核的“捷径”,本质是治理指标与乡村实际脱节下的被动选择。
驱动村长谈论科技刷赞的核心动力,是资源竞争中的“数字政绩焦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类政策红利、社会资本加速向乡村流动,但资源的分配往往与“数字化表现”挂钩——短视频播放量高的村子更容易获得文旅项目支持,政务APP活跃度高的乡镇能优先试点智慧农业。这种“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机制,本意是激励乡村创新,却催生了“唯数据论”的异化现象。一位东部沿海村长在内部工作群直言:“隔壁村靠刷赞拿到了‘网红村’称号,县里直接拨款搞民宿,咱们老老实实做内容,数据上不去,项目就黄了。”在这种竞争压力下,科技刷赞从“潜规则”变成“公开的秘密”,甚至被部分基层干部视为“数字时代的包装术”,认为只要最终能带动乡村发展,“数据美化”无伤大雅。这种逻辑的背后,是考核体系对“过程真实”与“结果导向”的失衡,以及对乡村数字化复杂性的低估——当刷赞成为能力标配,真正沉下心搞产业、办实事的村子反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科技刷赞的蔓延,更暴露出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真正的乡村数字化,应是利用科技提升治理效率(如智慧党建、农产品溯源)、促进产业融合(如直播带货、乡村旅游数字化)、增强村民参与(如在线议事、政务公开)。但在实践中,许多乡村的数字化停留在“表面功夫”:重硬件轻运营、重数据轻内容、重展示轻实效。某农业大省的乡村振兴报告显示,该省60%以上的村级政务新媒体账号存在“僵尸化”问题,日常内容多为转发上级通知,原创率不足10%。当缺乏持续的内容生产和精准的用户运营,刷赞便成了维持账号“活跃度”的最廉价方式。更关键的是,乡村数字人才匮乏——既懂技术又懂乡村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导致村长们面对数字化考核时,只能选择“走捷径”。正如一位村长所说:“我们想搞直播卖农产品,但没人会剪视频、做推广,刷点赞至少能让领导看到‘我们在努力’,不然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科技刷赞的短期“便利”背后,隐藏着长期的治理风险。 对村民而言,当村务宣传数据与实际感受严重脱节,会削弱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明明村里道路还是泥泞小路,短视频却宣称“村村通柏油”;明明农产品滞销,直播却显示“秒空光”。这种“数据幻觉”会加剧村民与干部之间的信息隔阂,甚至引发“狼来了”效应,未来即使有真实有效的数字化举措,也可能被质疑“又是在刷数据”。对乡村产业而言,虚假流量带来的“网红效应”往往是昙花一现:依赖刷赞吸引的游客可能因体验不佳而差评,靠数据包装的农产品品牌一旦被曝销量造假,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更严重的是,科技刷游走在平台规则与政策红线的边缘,若被认定为“数据造假”,不仅村集体可能面临处罚,基层干部的个人诚信也会受损。
要破解“村长谈论科技刷赞”的困局,需从考核机制、能力建设、数字伦理三方面同步发力。在考核端,应建立“重实效轻形式”的数字化评价体系,将村民满意度、产业实际收益、治理效率提升等“硬指标”纳入核心考核维度,减少对“点赞量”“粉丝数”等表面数据的依赖。在能力端,需加大对乡村数字人才的培育力度,通过“返乡青年培训+科技特派员下沉”模式,让村长们掌握内容创作、用户运营、数据分析等实用技能,从“被动刷赞”转向“主动运营”。在伦理端,则要引导基层树立“数字向善”意识,明确科技是工具而非目的——数字化的价值不在于数据多漂亮,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乡村发展中的痛点,让村民在数字时代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归根结底,村长谈论科技刷赞,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成长阵痛”。它提醒我们:数字乡村建设不能搞“一刀切”的指标摊派,也不能脱离乡村实际搞“空中楼阁”式的数字化。唯有扎根乡土需求,尊重治理规律,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才能避免“刷赞”沦为基层治理的“伪命题”,让数字化的阳光照亮乡村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