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和马克思主义有啥区别,关系到底是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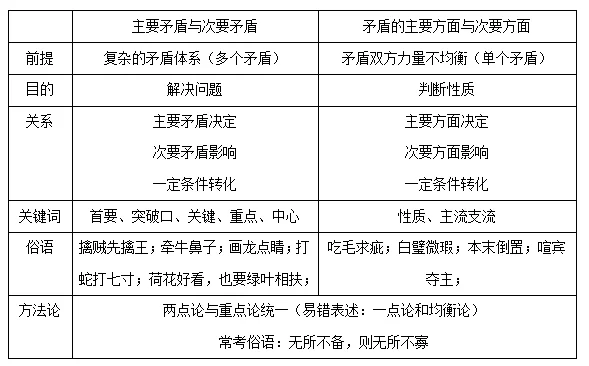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并非其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而仅仅是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值(即维持劳动者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者在工作日中,一部分时间用于再生产自身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而其余时间则无偿为资本家创造价值(剩余劳动时间),这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利润的源泉。将这一范式应用于兼职领域,其内在逻辑便清晰可见。无论是利用业余时间送外卖、做设计,还是运营自媒体账号,兼职者一旦进入市场交换,其劳动便成为商品。平台或雇主支付的报酬,同样遵循着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兼职者获得的“时薪”或“项目费”,本质上是对其劳动力价值的购买,而其劳动成果所蕴含的更大价值,则被平台、品牌方或最终的资本所有者所攫取。即便兼职者感到“多劳多得”,获得了比本职工作更高的时薪,也无法改变其在剩余价值被剥削上的结构性地位。这种剥削的隐蔽性在于,它常常被“合作”、“共赢”、“自我实现”等话语所包装,让劳动者误以为自己是在为自身价值而奋斗,从而模糊了雇佣关系的本质。
如果说剩余价值的揭示还停留在经济层面,那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则触及了兼职现象对“人”的更深层次的冲击。异化,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劳动产品、自身类本质乃至他人相分离的状态。在“零工经济”催生的兼职浪潮中,这种异化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一名兼职的网约车司机,其劳动产品是“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这一服务,但他无法拥有、控制甚至识别这项服务的完整价值,它被算法、平台和资本所分割。其次,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兼职工作往往被高度碎片化、标准化和算法化。外卖骑手的路线由算法规划,内容创作者的选题受平台流量牵引,劳动不再是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活动,而是一种被动、机械、受外部指令支配的过程。再次,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许多兼职中,劳动的目的被简化为纯粹的生存手段,它压抑了人的创造力和潜能,使人无法在劳动中确证和发展自我,最终感到疲惫、空虚而非满足。最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平台化的兼职模式将劳动者原子化,他们不再是工厂里并肩作战的同事,而是算法系统下相互竞争的“独立承包商”。这种缺乏集体连结的状态,极大地削弱了劳动者形成集体意识、进行阶级团结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分析,一个理论问题随之而来:兼职者是否属于无产阶级范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无产阶级的判定标准并非工作时长或收入多寡,而是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生存的劳动者,就属于无产阶级。循此标准,绝大多数兼职者无疑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不拥有平台、数据、厂房、资本,他们拥有的仅仅是自身的劳动能力。他们从事兼职,往往是由于单一的全职工作已无法满足其生活需求,这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劳动力价值被系统性压低的现实反映。因此,兼职现象的普遍化,可以被视为无产阶级在当代社会的一种生存形态的演变,甚至可以借用“不稳定无产者”这一概念来描述其特征:他们缺乏传统雇佣关系下的稳定保障,时刻面临着市场的风吹草动,生活处于一种持续的不确定状态之中。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中产”、“白领”、“自由职业者”等身份迷思,将看似多元的职业选择重新拉回到阶级分析的框架内,揭示出其共同的阶级基础与处境。
那么,在认清了兼职背后的剥削与异化本质后,我们是否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境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最终指向的是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探讨个人价值的实现,并非否定兼职者在现实处境中为改善生活所做的努力,而是要思考一条通往真正解放的道路。首先,价值实现的主体性觉醒是第一步。当劳动者能够意识到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能够识别出工作中的异化状态时,意识形态的迷雾便开始消散。这种“觉悟”本身,就是摆脱物化、重拾主体性的开端。其次,集体行动与权利斗争是必由之路。个体的、零散的兼职者面对庞大的资本平台是弱势的,唯有通过组织化,例如组建或加入工会、行业协会,进行集体谈判,争取更合理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才能有效制衡资本的力量。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零工经济工作者发起的维权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个人价值的彻底实现,有赖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到那时,“兼职”这一为生存而被迫进行的额外劳动,将自然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在此之前,每一次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每一项关于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立法,都是在为那个更理想的未来奠定基石。兼职者在当下的每一次抗争与自我意识的提升,都是在参与一场宏大的历史进程,其意义远超个人收入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