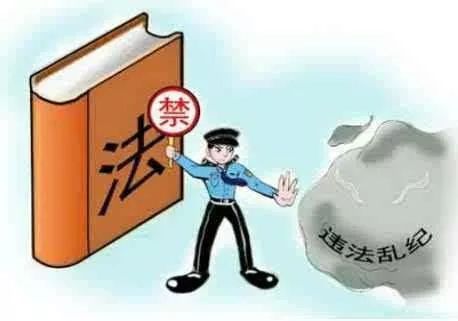
找水军刷赞的行为,本质上是对互联网信息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其违法性早已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得到明确界定。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虚假流量、刷单炒信等乱象成为监管重点,而“找水军刷赞”作为其中典型,不仅违背商业道德,更直接触碰了法律红线。从法律定性到社会危害,从监管难点到合规路径,这一行为的违法性需要从多维度进行深度剖析,以厘清认知、震慑违法,为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一、法律定性: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的复合违法
找水军刷赞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具有明确的复合违法性,其核心在于通过虚构用户评价、制造虚假热度,欺骗误导消费者,同时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找水军刷赞,正是通过组织“水军”批量制造虚假点赞、好评,虚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反响,属于典型的“虚假用户评价”行为,直接违反该条款。
进一步看,若刷赞行为涉及电子商务领域,则更需适用《电子商务法》的严格规制。该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刷赞行为通过虚假数据掩盖真实商品或服务质量,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可能构成《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禁止的“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违法行为,依据第八十五条,面临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
此外,《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也为打击刷赞行为提供了依据。《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诈骗、教唆犯罪”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而组织水军刷赞可能涉及非法经营(如提供刷赞服务)或帮助他人虚假宣传,已超出合法经营边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则明确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虚假信息”,刷赞行为制造的虚假热度,本质上是对互联网信息真实性的破坏,违反该规定。
二、危害蔓延:从市场失序到信任危机的多重冲击
找水军刷赞的危害远不止于“违反法律”的表层标签,其负面影响已渗透至市场、消费者、平台乃至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形成连锁破坏效应。在市场层面,刷赞行为通过制造“虚假繁荣”,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优质内容或服务本应通过真实价值获得用户认可,而刷赞却让劣质商品或低质内容“劣币驱逐良币”——某商家投入数万元找水军刷赞,即可在短期内获得平台流量倾斜,挤压了依靠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获取市场份额的企业的生存空间。这种“数据造假”导致的资源错配,长期将削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阻碍行业高质量发展。
对消费者而言,刷赞行为直接侵害了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用户在浏览商品或内容时,往往会参考点赞量、好评率等指标作为决策依据,而虚假点赞则构建了一个“信息茧房”:消费者被误导购买低质商品,或关注缺乏价值的账号,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可能因信任落差对互联网生态产生负面认知。例如,某网红餐厅靠刷赞成为“网红打卡地”,消费者到店后发现服务差、口味差,引发大量投诉,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网红推荐”的整体信任度下降,这种信任危机的修复成本极高。
对平台而言,刷赞行为破坏了算法推荐机制的准确性。如今,抖音、小红书、淘宝等平台均依赖算法分析用户行为与内容热度,而虚假点赞数据会污染算法模型,导致优质内容无法触达真实用户,低质内容却因“虚假热度”获得流量倾斜。长此以往,平台用户体验下降,活跃度降低,最终损害平台自身的商业价值。此外,刷赞行为还可能滋生黑色产业链,如“水军”组织通过批量注册虚拟账号、使用外挂软件刷赞,涉及个人信息盗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衍生犯罪,进一步加剧互联网治理难度。
三、监管挑战:隐蔽性、技术性与跨平台性的博弈
尽管法律法规对刷赞行为的违法性已有明确规定,但实际监管中仍面临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行为的隐蔽性、技术迭代速度与跨平台特性。从隐蔽性看,“水军”组织通常采用“去中心化”运作模式,通过社交群组、暗网等渠道接单,使用虚拟账号、境外服务器、加密通信工具进行交易,资金流转也多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洗白”,导致监管部门难以追踪源头。例如,某“水军”团伙通过微信小群接单,用不同手机号注册大量虚拟账号,通过模拟人工点赞完成刷赞任务,单笔交易金额小、频次高,常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拦截。
技术迭代则让刷赞手段不断“升级”。早期刷赞依赖人工点击,如今已发展为AI模拟、自动化脚本、云控设备等技术手段。例如,通过AI程序模拟用户点赞行为(包括随机切换IP、模拟滑动轨迹、间隔时间等),可绕过平台的基础风控系统;部分不法分子甚至利用“手机农场”(集中管理大量实体手机设备)进行24小时不间断刷赞,技术复杂度远超传统监管能力。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技术博弈,对监管部门的科技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
跨平台性也增加了监管难度。刷赞行为往往涉及多个平台:需求方在A平台发布内容,水军从B平台接单,通过C平台的支付工具转账,数据造假发生在D平台的账号体系。这种“跨平台协作”模式导致监管责任分散,不同平台间的数据共享与执法协作机制尚不完善,容易出现“监管真空”。例如,某商家在抖音找水军刷赞,水军通过微信支付转账,数据存储在第三方服务器,监管部门需协调抖音、微信、服务器提供商等多方才能获取完整证据链,执法效率大打折扣。
四、合规路径:构建“法律-平台-用户”共治体系
面对找水军刷赞的违法性与治理挑战,需从立法完善、平台责任、用户意识、技术手段等多维度发力,构建“法律为基、平台为盾、用户为眼、技术为刃”的共治体系。
在立法层面,需进一步细化刷赞行为的法律责任与认定标准。当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虽已明确禁止,但对“水军”组织者、需求方、平台连带责任的划分仍需更清晰的指引。例如,可借鉴《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中对虚假宣传的处罚细则,明确“刷赞服务提供者”的非法经营性质,对组织者设定更高罚款额度;对明知故犯的需求方(如商家),可纳入“信用中国”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同时,推动出台《互联网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将“虚假流量”纳入数据造假范畴,明确其危害性与处罚依据。
平台作为互联网内容与服务的“守门人”,需承担主体责任。一方面,应加大技术投入,建立“反刷赞”智能风控系统。例如,通过机器学习分析用户点赞行为特征(如同一IP短时间内多次点赞、设备指纹重复、无浏览行为的“秒赞”等),识别异常流量;引入区块链技术对用户评价数据进行存证,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实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另一方面,完善内部举报与处置机制,对查实的刷赞账号采取封禁、限流等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送线索,形成“平台自治+行政监管”的联动闭环。
用户作为互联网生态的参与者,其辨别与举报意识至关重要。平台需通过弹窗提示、教育专栏等方式,向用户普及“刷赞”的危害性,教用户识别虚假流量(如点赞量与评论量严重不符、账号注册时间短、无历史互动等异常特征)。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对有效举报用户给予奖励,鼓励用户参与治理。例如,小红书曾推出“虚假流量举报入口”,用户可举报异常点赞账号,经核实后给予平台积分奖励,有效调动了用户积极性。
监管部门则需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提升监管效能。可建立“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的联合执法机制,共享“水军”组织者、支付账号、服务器IP等数据,实现“线索发现-调查取证-打击处置”的全链条监管。同时,加强对新兴技术的监管研究,例如针对AI刷赞、云控设备等手段,提前制定技术识别标准与应对预案,避免监管滞后。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真实性是市场秩序的基石,每一份点赞都应承载真实的价值判断。找水军刷赞的行为,看似是“快速见效”的营销捷径,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破坏生态平衡的违法行为。唯有以法律为利剑,以技术为盾牌,以共治为纽带,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让互联网回归“真实、透明、有序”的本真,让每一份努力都获得真实认可,让每一份信任都不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