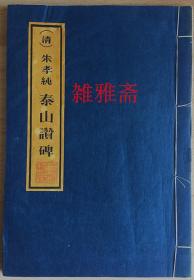
清代刷赞网并非现代互联网语境下的虚拟平台,而是对清朝社会中各类“声誉营造”行为的统称——一种通过人为干预、群体合谋或资源置换,系统性提升个人、家族、商品或官方事务“公众评价”的社会现象。在科举制度、宗族社会与商业经济交织的清代生态中,这种“刷赞”行为早已渗透至士林、市井、官场乃至宫廷,成为影响社会流动、文化生产与权力运作的隐性机制。其存在并非简单的道德失范,而是传统社会结构下声誉评价体系与资源分配逻辑的必然产物,折射出清代社会在“名实之辨”上的深刻张力。
一、清代刷赞网的三重形态:从文人墨客到市井商贾
清代刷赞网的实践形态,首先活跃于士林文化圈。在科举取士的核心赛道上,“文名”往往是仕途的敲门砖,于是催生了“文场吹捧”的产业链。文人通过诗社、文会结成利益共同体,互相品鉴诗作、撰写序跋,甚至形成“流派互捧”的风气——如桐城派与阳湖派在文坛的竞争,不仅是文学理念的差异,更暗含通过群体声誉叠加提升流派地位的现实考量。更有甚者,部分落第文人或低级官员以“代笔”“润色”为业,为富家子弟或地方名流炮制制义、诗集,再通过书坊刊行、文人题跋制造“洛阳纸贵”的假象,实质是一种以文化资本换取社会声誉的“刷赞”操作。这种操作虽不直接等同于现代“刷流量”,却通过构建“文化权威”的虚假表象,深刻影响了清代文坛的生态。
其次,市井商业领域的“商誉营造”构成了刷赞网的第二条主线。清代商品经济繁荣,招牌字号成为商家的核心资产,于是“口碑操纵”应运而生。茶楼、酒肆、绸缎庄等商业机构,常雇佣“闲汉”或“媒婆”在市井间散布“某店货真价实”“某铺童叟无欺”的赞誉,甚至伪造“官府告示”“名人题匾”增强公信力。例如苏州的“绣娘一条街”,绣品质量的竞争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文人题赞”“闺阁传名”的较量——富家小姐以拥有某绣娘的作品为荣,绣坊便通过小姐们的社交圈扩散“名绣”声誉,实质是以社会精英的“点赞”背书商业价值。这种商业刷赞虽带有欺骗性,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行业标准的精细化,只是当“刷赞”过度脱离商品实际品质时,便催生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市场乱象。
最后,官方治理领域的“政绩修饰”构成了刷赞网的最高层级。清代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依赖“政声”,于是“数据美化”“舆论引导”成为官场潜规则。地方官为博取“清廉”“能干”的赞誉,一方面通过乡绅、族长收集“民意”,编纂“德政碑”“去思录”;另一方面在灾荒、河工等事务中虚报成效,甚至联合上级官员“奏销浮夸”,将“减产”报为“丰收”,“民怨”饰为“民颂”。如雍正年间推行的“火耗归公”,本是一项整顿吏治的改革,但部分地方官为营造“政绩斐然”的假象,强行摊派火耗,反而加重百姓负担,其“清誉”背后实则是权力与“刷赞”合谋的扭曲产物。这种官方刷赞不仅损害了治理实效,更侵蚀了朝廷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基础。
二、清代刷赞网的社会地位:权力结构的镜像与资源分配的润滑剂
清代刷赞网的社会地位,本质是传统社会“人情社会”与“等级社会”双重属性的投射。在以“血缘”“地缘”“学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中,“声誉”并非客观评价,而是人际关系互动的结果,刷赞行为因此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对士大夫阶层而言,“文名”“官声”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刷赞既是维护阶层利益的工具,也是应对科举竞争、官场倾轧的生存策略——正如清代笔记《郎潜纪闻》中所言:“士人重声名,然声名非空穴来风,必赖朋党援引、舆论吹嘘,方能显达于世。”这种认知使得刷赞在士林中被视为“常态”,甚至被包装为“雅事”,如文人间的“互赠诗文”“品题书画”,表面是风雅酬唱,实则是声誉资本的交换。
对商业社会而言,刷赞则是打破信息不对称、获取市场信任的无奈之举。清代市井民众识字率低,商品质量多依赖口碑传播,而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刷赞成为跨越鸿沟的“捷径”。这种“商誉营造”虽可能短期欺骗消费者,但长期来看,它迫使商家在“刷赞”与“品质”间寻求平衡——真正能立足的商号,仍需以“真材实料”支撑虚假的“赞誉”,客观上推动了商业诚信的萌芽。例如北京的同仁堂,早期也曾通过“御药供奉”的官方赞誉打开市场,但最终依靠“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祖训维系声誉,说明刷赞只能是商业成功的“敲门砖”,而非“立身之本”。
对官方体系而言,刷赞则成为皇权与地方社会互动的“润滑剂”。清代统治者强调“以孝治天下”“以农为本”,地方官的“德政”评价直接关系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刷赞行为在此背景下被默许甚至鼓励。如康熙帝南巡时,地方官提前布置“民戴德政”的场景,百姓举香跪迎,实则是官府组织的“舆论秀”,但这种“刷赞”却强化了“皇恩浩荡”的政治叙事,巩固了中央权威。只是当刷赞过度演变为“欺上瞒下”时,便成为官场腐败的温床——乾隆年间的“甘肃冒赈案”,地方官员通过虚报灾情、伪造“民赞”贪污赈银,最终导致数十名官员被处,揭示了官方刷赞对统治根基的潜在威胁。
三、清代刷赞网的悖论:表面繁荣下的社会信用危机
清代刷赞网的盛行,虽在短期内催生了文化、商业的“虚假繁荣”,却长期侵蚀了社会的信用基础,形成了“名实分离”的恶性循环。在文化领域,过度依赖“文人吹捧”导致作品质量与声誉脱节,部分文人将精力耗费于“结党营私”“品题应酬”,而非潜心创作,使得清代文学虽流派纷呈,却鲜有突破性成就。正如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批判的:“近世文人,竞以标榜为能,而实学益荒。”这种“重名轻实”的风气,最终导致文化创新乏力。
在社会层面,刷赞行为的普遍化加剧了“信任赤字”。当民众发现“德政碑”可能是官员伪造,“口碑”可能是金钱买来,“文名”可能是群体吹捧时,社会评价体系便陷入“塔西佗陷阱”——无论真实信息还是虚假信息,民众皆不再相信。这种信任危机不仅破坏了人际关系的真诚性,更削弱了社会协作的效率,使得清代社会在面对自然灾害、外部冲击时,缺乏有效的动员能力。
在政治领域,刷赞与腐败的深度绑定,加速了王朝的衰亡。晚清时期,官场“以誉取人”的风气愈演愈烈,官员将“钻营”“逢迎”视为获取声誉的手段,而将“实政”“民生”抛诸脑后。如鸦片战争前,两广总督李鸿宾为营造“海疆安定”的政绩,隐瞒英国军舰入侵的实情,反而通过“奏报海晏河清”获得道光帝的“赞誉”,最终导致战事准备不足,丧权辱国。这种“刷赞误国”的悲剧,正是清代刷赞网走向极致的必然结果。
清代刷赞网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其存在与演变,本质是传统社会结构中“声誉机制”与“资源分配”相互作用的缩影。它既反映了士大夫、商人、官员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也暴露了传统社会在信用构建上的深层缺陷。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镜像时,不仅要警惕“刷赞”行为对现代社会诚信体系的侵蚀,更需思考:如何构建一种让“实绩”而非“虚名”、让“诚信”而非“逢迎”成为评价核心的社会机制?这或许是清代刷赞网留给当代最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