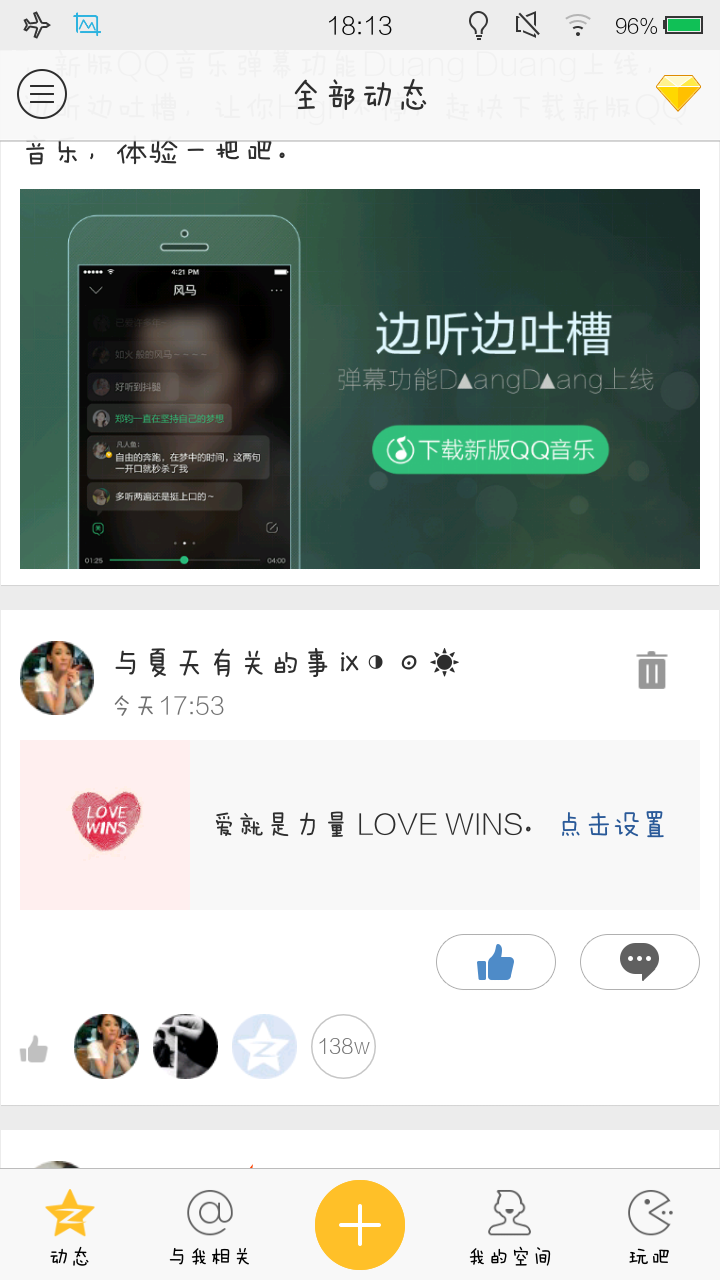
“最美新生评选”本应是展现大学生风采、传递校园正能量的平台,近年来却屡屡陷入“刷赞风波”——榜单上高票数的背后,是批量注册的“僵尸号”、明码标价的“点赞套餐”,甚至演变为班级间的“数据竞赛”。这种异化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评选机制、流量逻辑与参与者心理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要破解这一困局,需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而非简单归咎于“学生素质问题”。
唯数据论的评选机制是刷赞现象的制度根源。当前多数“最美新生”评选将“点赞量”“转发量”作为核心指标,甚至将其与奖学金、荣誉称号直接挂钩,形成“数据至上”的价值导向。某高校2023年评选规则中,点赞数占比高达70%,剩余30%为“基础分”(如学生证、录取照片),这种设计本质上将评选简化为“数据竞赛”。当“美”的内涵被窄化为“被点赞的数量”,参与者自然会将精力转向如何提升数据而非展现真实风采。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平台为追求流量,刻意设置“实时排名”“倒计时冲刺”等刺激性功能,加剧了参与者的焦虑感——在“不刷就落后”的集体无意识中,刷赞从“潜规则”演变为“明规则”。
流量经济的逐利本性为刷赞行为提供了生存土壤。校园评选看似“非营利”,实则已深度嵌入流量经济的产业链条。一方面,校园媒体、学生会组织为提升账号影响力,通过“评选话题”吸引流量,再将流量转化为广告收益或资源倾斜;另一方面,第三方商家嗅到商机,推出“刷赞服务”:10元100赞、50元1000赞,甚至提供“真人点赞”“IP切换”等“高级套餐”。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开学季期间,“校园刷赞”相关搜索量同比激增300%,形成“学生需求-商家供给-平台默许”的畸形生态。在这种逻辑下,评选不再是“选美”,而是“流量生意”,而刷赞者、平台、商家共同构成了利益共同体,普通学生则沦为流量收割的“工具人”。
新生群体的心理需求与社交焦虑为刷赞提供了心理动因。刚入学的新生正处于身份认同的关键期,渴望通过“被认可”建立自信、融入集体。“最美新生”评选恰逢其时地提供了“社交货币”——高票数意味着“受欢迎”“有魅力”,甚至可能带来辅导员关注、同学崇拜等隐性收益。心理学中的“社会比较理论”在此显现:当看到身边同学通过刷赞迅速提升排名,个体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为避免落后而加入刷赞大军。某调查显示,78%的参与承认“刷赞是怕被同学议论”,63%认为“大家都刷,我不刷就吃亏”。这种从众心理与群体压力,使得刷赞从“个别行为”扩散为“集体现象”,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真正用心展现风采的学生,可能因“不屑刷赞”而被淹没在数据泡沫中。
技术监管的滞后与制度惩戒的缺位,让刷赞行为几乎“零成本”。当前校园评选多依赖微信、微博等第三方平台,而这些平台的反作弊系统主要针对商业营销,对校园场景的“小规模、精准化”刷赞识别能力不足。例如,通过“校园代理”组织的真人点赞,使用不同设备、不同IP地址,能有效规避平台检测。更关键的是,多数评选缺乏明确的惩戒机制:即使发现刷赞,往往仅取消资格而未追溯责任,甚至因“顾及学校声誉”而“内部消化”。某高校曾曝出“刷赞黑产”,但最终仅以“取消前五名资格”收场,组织者未受任何处罚。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博弈结构,让刷赞者有恃无恐,也让评选公信力荡然无存。
当“最美新生”的桂冠不再由点赞数定义,当真正的青春风采在多元评价中绽放,校园评选才能回归其初心——不是一场数据的狂欢,而是一次精神的共鸣。这需要重构评价体系:将志愿服务、学业表现、才艺特长等“质化指标”纳入核心权重,引入师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团进行匿名评审;需要切断流量利益链,明确禁止商业机构参与评选,建立平台、学校、学生三方联动的监督机制;更需要引导学生树立“美是多元的”认知,让“最美新生”成为“真实、善良、勇敢”的代名词,而非“点赞数”的傀儡。唯有如此,评选才能真正成为照亮新生大学生活的第一束光,而非异化为流量时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