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禁止干副业,6类具体是哪些,中纪委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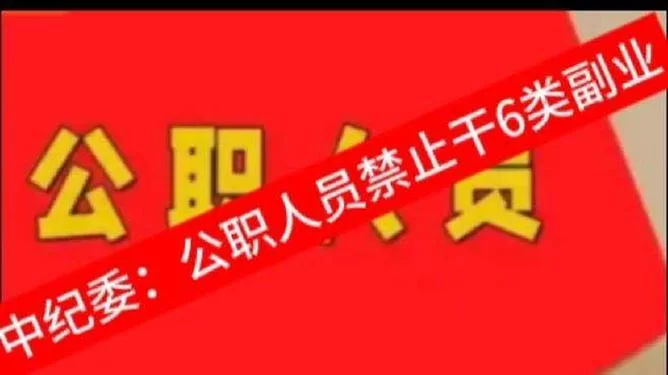
在公众的普遍认知里,“公职人员禁止干副业”是一条清晰的纪律红线。然而,当具体问及哪些行为属于被禁止的“副业”时,许多人却感到模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中纪委明确6类副业禁区”的说法,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这一说法并非源自中纪委某份单一文件的直接罗列,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中相关禁止性条款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理解这些规定的深层逻辑与具体内涵,对于每一位手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而言,不仅是避免纪律处分的“护身符”,更是保持初心、廉洁从政的“必修课”。
为何要划定如此严格的“副业”禁区?其核心要义在于防范利益冲突,维护公权力的纯洁性。公职人员的薪酬由国家财政保障,其职责是为人民服务,而非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一旦允许其随意从事营利性活动,手中的权力便极易与市场利益勾连,滋生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腐败土壤。因此,从制度层面斩断公职人员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之间的不当连接,是构建清明政治生态的基石。这六类禁区,正是围绕这一核心原则构建的立体防护网。
第一类:违规经商办企业。这是最为典型和明确的禁止行为。它不仅指公职人员亲自注册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以他人名义代持股份、暗中合伙经营等更为隐蔽的形式。无论是开设实体店、创办科技公司,还是投资入股朋友的企业,只要参与了具体的经营管理或持股分红,都属于违规经商办企业。此类行为直接将公职人员置于“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第二类:违规兼职取酬。这里的“兼职”特指在营利性组织或社会团体中担任职务并获取报酬。例如,在企业担任顾问、专家,领取咨询费或津贴;在行业协会等社团兼职,领取工资。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鼓励公职人员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从事教学、科研、写作等非营利性社会活动,并可以取得合法报酬,但前提是必须经过组织批准,且不得影响本职工作,更不能利用职务影响力为自己或兼职单位谋取利益。未经批准的兼职取酬,或虽经批准但违规取酬,都在禁止之列。
第三类:从事有偿中介活动。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利益输送方式。公职人员利用其身份、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在交易双方之间充当“掮客”,撮合交易并从中收取“好处费”、“中介费”。例如,利用分管工程建设的便利,为承包商介绍项目并抽取佣金;利用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优势,为企业代办许可并收取高额费用。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贩卖”公权力,是对职务廉洁性的严重侵蚀。
第四类: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进行其他证券投资。此项规定具有特殊性,并非“一刀切”地禁止所有公务员炒股。根据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司法机关等特定部门的公职人员,以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买卖股票。其他公务员则可以买卖股票,但严禁利用内幕信息、掌握的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严禁收受上市公司赠送的原始股,严禁利用职权影响股票价格。这一规定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精准打击了与公职身份直接相关的金融腐败风险。
第五类: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或者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些公职人员试图将资产转移至境外,通过在境外开办公司、投资入股等方式隐匿财产、逃避监管。此类行为不仅违反了廉洁纪律,更可能涉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法规对此类行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第六类:其他违反规定的营利活动。这是一个兜底条款,旨在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形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一些新型的“副业”形式层出不穷,如网络直播带货、知识付费、担任网红博主等。这些行为是否违规,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利用了公职身份或职务影响力进行营利,是否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例如,一名法官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付费法律咨询服务,即便内容专业,也因其特殊身份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而被视为违规。
厘清禁区之后,人们自然会问:公务员完全不能有任何“副业”吗?答案并非绝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保护。法规允许的是不影响廉洁性、不与公权力冲突的合规性收入。例如,通过继承或赠与获得的财产性收益;在不影响本职工作并经组织批准后,从事教学、科研、书画创作等智力活动取得的稿酬、讲课费;以及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合法储蓄、理财等。关键在于“阳光”与“报备”。任何可能产生疑问的收入来源,都应主动向组织报告,接受监督,这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纪律的敬畏。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对公职人员从事营利活动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越来越细。大数据技术让隐性持股、代持等行为无所遁形,金融监管的强化也让违规证券投资难逃法眼。对于每一位公职人员而言,与其绞尽脑汁寻找纪律规定的“灰色地带”,不如从一开始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价值观。那些看似能够带来额外收入的“副业”,往往通向的是纪律的深渊和人生的歧途。公职人员的价值,不在于积累多少个人财富,而在于为公众创造了多少福祉,为社会发展贡献了多少力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这份职业本身带来的荣誉感与成就感,远非任何物质利益所能比拟。这份职业的荣光,恰恰源于其对私利的克制与对公利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