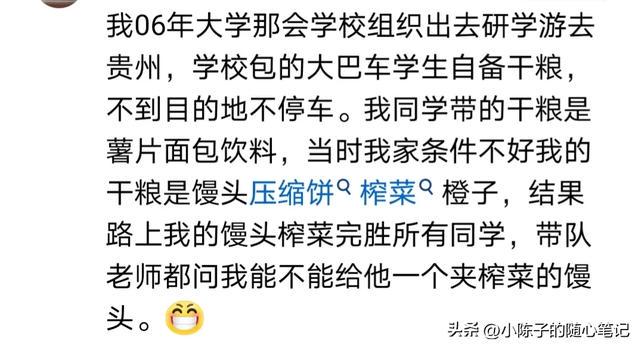
萌宝刷赞行为,早已不是社交媒体的偶然现象——当幼儿园孩子熟练滑动屏幕只为给朋友的视频点个赞,当父母晒出孩子“点赞小达人”的截图收获一片羡慕,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的,是儿童社交心理、家庭教养逻辑与平台商业逻辑的复杂交织。萌宝刷赞行为的本质,是儿童在数字时代寻求社会认同的初级尝试,却也折射出成人世界对“可爱经济”的过度消费与引导偏差。
儿童对点赞的渴望,并非天生而来,而是在模仿与强化中逐渐习得。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3-6岁的儿童正处于“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期,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外部反馈确认“我是谁”“我是否被喜欢”。点赞作为一种即时、具象的积极反馈,恰好满足了他们对“社会认同”的原始需求。当孩子给同学的画作点个赞,对方回以一个笑脸表情时,他们会直观感受到“我的行为能让别人开心”,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会强化他们的点赞行为。更关键的是,儿童的学习方式以“观察模仿”为主,而父母正是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当家长频繁展示自己通过朋友圈点赞获得社交互动,甚至用“宝宝快给阿姨点个赞,阿姨会给你买糖”进行引导时,孩子会自然将“点赞”与“获得认可”“获得奖励”绑定,逐渐将这一行为内化为社交“必修课”。
如果说儿童的模仿行为是内因,那么平台的算法设计则是外因的催化剂。当前主流社交媒体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注意力经济”与“反馈机制”的结合体。点赞按钮的显眼位置(如视频右下角的红色心形图标)、点击后的动态效果(如小红心飞出、数字+1的即时反馈),都暗合了游戏化设计中的“即时奖励”原则——这种设计对缺乏自控力的儿童尤其具有吸引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平台算法会优先推送高互动内容,而“萌宝”类内容天然具有流量优势:一张孩子吃蛋糕的憨态照片、一段蹒跚学步的萌趣视频,往往能轻松获得远超普通内容的点赞量。这种“高点赞=高价值”的隐性评价,会让孩子和家长形成“萌宝必须被点赞”的心理预期,甚至为了维持“高赞人设”而刻意引导孩子刷赞。
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第一环境,其教养方式直接塑造了孩子对点赞的认知。在“展示型育儿”盛行的当下,不少家长将孩子视为社交媒体的“内容素材库”,从“宝宝第一次翻身”到“幼儿园表演节目”,事事都要分享并期待点赞回应。当孩子主动提出“妈妈,你快帮我点赞”,家长非但没有纠正,反而以“我们宝宝真受欢迎”进行鼓励,实则是在向孩子传递“点赞多少等于受欢迎程度”的错误价值观。更有甚者,部分家长会通过“买赞”“刷量”等方式为孩子内容造假,这种“虚假繁荣”不仅让孩子混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更让他们学会用数据而非真诚来衡量社交关系。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为了获得点赞而刻意“表演”,甚至失去自然表达的兴趣——毕竟,真实的快乐远不如100个点赞带来的“成就感”来得直观。
社会文化中“可爱经济”的推波助澜,进一步放大了萌宝刷赞行为的普遍性。在消费主义逻辑下,“萌”早已成为一种可被量化的商业资源:品牌方争相邀请萌宝代言,商家通过“萌宝点赞抽奖”活动引流,甚至连教育机构都打出“点赞最多送课程”的营销口号。这种“可爱=流量=利益”的链条,让萌宝的社交行为被不断工具化。当孩子发现“原来我点赞能帮妈妈赚钱”“点赞多就能得到玩具”,他们参与刷赞的动力便从“社交需求”异化为“利益交换”。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异化可能扭曲儿童的价值观——他们可能过早学会用“讨好”换取关注,而非通过真实的情感连接建立社交关系,这与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
萌宝刷赞行为看似 harmless,实则是对儿童社交认知的早期干预。当点赞成为孩子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尺,当“被喜欢”取代“真实的表达”,数字时代的童年正在被悄然异化。 家庭需警惕“展示型育儿”的陷阱,将关注点从“孩子的点赞数”转向“孩子的真实快乐”;平台应承担起儿童社交环境的净化责任,通过“青少年模式”限制点赞功能,减少算法对儿童的负面影响;而社会也需重新审视“可爱经济”背后的伦理边界——毕竟,孩子的童年不该成为点赞数据里的一串数字,他们有权在真实而非虚拟的认同中,慢慢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