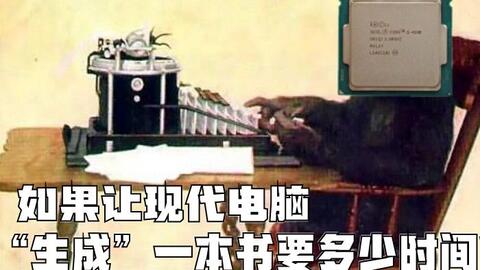
1980年代的“刷赞现象”,并非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游戏,而是社会转型期中,个体对集体认可的本能追逐在特定物质与精神条件下的具象化表达。这一现象的诞生,既非偶然的道德失范,也非简单的“虚荣心作祟”,而是植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结构性矛盾、信息传播媒介的单一性、以及集体主义价值观松动后个体价值认同的真空地带。要理解这一现象的生成逻辑,必须将其置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语境中,从制度变迁、媒介生态、文化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社会结构转型:单位制松动与“认可资源”的稀缺性
19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从“单位制”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过渡的初期。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的生存资源(住房、医疗、教育等)几乎完全依附于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是价值分配与认可的绝对中心。此时的“认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被单位领导“点赞”,意味着晋升机会、福利分配乃至社会地位的提升。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逐渐活跃,个体开始从单位中“解放”,但新的社会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标准”尚不明确,而传统单位内的“认可机制”因体制改革的推进而逐渐弱化。这种“旧秩序瓦解、新秩序未立”的过渡状态,导致“认可资源”出现严重稀缺——个体既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如财富、职业成就)快速获得身份认同,又难以在单位中延续过去的“被点赞”路径。于是,“人工刷赞”作为一种替代性策略应运而生:人们通过人情往来、关系运作,甚至在正式场合(如会议、评优)中刻意表现,以“制造”被认可的假象,填补价值认同的真空。这种“刷赞”本质上是转型期个体对“安全需求”与“尊重需求”的本能回应,是在制度缝隙中争夺稀缺认可资源的生存智慧。
媒介生态限制:纸质媒介霸权与“点赞”的具象化表达
与互联网时代“点赞”的即时性、虚拟性不同,1980年代的“刷赞”必须依赖实体媒介,其形态更接近于“公开的书面认可”或“口头的集体赞扬”。这一时期的媒介生态呈现“纸质霸权”特征:报纸、杂志、内部刊物、单位简报等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点赞”的主要发生场景。由于大众传媒渠道有限(电视尚未普及,广播影响力有限),个体若想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必须通过“被印刷”或“被点名”的方式——一篇报道、一则表彰通知、一次会议发言,都可能成为“点赞”的实体化载体。这种媒介特性直接催生了“刷赞”的操作逻辑:为了获得纸质媒介的“点赞”,个体或群体会主动向编辑、记者投递事迹材料,甚至通过“人情稿”“关系稿”争取曝光机会;在单位内部,为了在简报上“被点赞”,人们会在会议发言中刻意拔高自身表现,或在评优活动中拉票、串联。此时的“刷赞”并非数字时代的流量造假,而是对“媒介稀缺性”的被动适应——当“被印刷”成为“被认可”的唯一通行证,“刷赞”便成为个体突破媒介壁垒、争夺话语权的无奈之举。值得注意的是,纸质媒介的“权威性”赋予了“刷赞”行为以正当性伪装:一篇刊登在党报上的表扬稿,其分量远超今天的百万点赞,这种“权威背书”使得“刷赞”在道德上具有了模糊空间,甚至被视为“积极表现”的合理延伸。
文化心理变迁:集体主义惯性下的个体价值焦虑
1980年代的文化心理,呈现出“集体主义惯性”与“个体意识觉醒”的剧烈碰撞。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集体主义教育,使得“服从集体”“追求荣誉”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让个体开始意识到“自我价值”的存在,但这种觉醒尚未形成成熟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人们既渴望摆脱集体对个体的压抑,又无法脱离集体获得意义感。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催生了“刷赞”的文化动因:在集体主义框架下,“被点赞”依然是衡量个体价值的核心标尺,但此时的“点赞”已不再是单纯对集体贡献的肯定,而是掺杂了个体对“独特性”的诉求。于是,“刷赞”行为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个体通过模仿集体的“点赞话语”(如“舍己为人”“爱岗敬业”)来获得认同,延续了集体主义的表达习惯;另一方面,又在“点赞”内容中刻意突出个人特质(如“创新精神”“业务能力”),试图在集体中彰显个体价值。这种“伪集体主义”的“刷赞”行为,本质上是个体在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挣扎——用集体的形式包装个体的欲望,以“被点赞”的方式确认“我存在”。正如社会学家所言,转型期的文化变迁总是滞后于制度变迁,当个体意识尚未获得制度性认可时,“刷赞”便成为其表达价值诉求的“畸形出口”。
回望1980年代的“刷赞现象”,它绝非简单的道德瑕疵,而是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的微观投射:在制度缝隙中,个体通过“人工方式”争夺稀缺的认可资源;在媒介限制下,将“点赞”具象化为实体的文字与符号;在文化冲突中,用集体的外衣包裹个体的焦虑。这一现象的历史启示在于:任何社会行为的发生,都深植于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土壤;而“点赞”的本质,终究是个体对价值认同的本能渴望。当社会能够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当媒介能够承载更丰富的个体表达,当个体价值能够获得制度性的尊重与保障,“刷赞”自然会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因为真正的“点赞”,从来不是人工堆砌的泡沫,而是价值生长的自然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