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有副业,和宰相有啥区别?蜀汉还有几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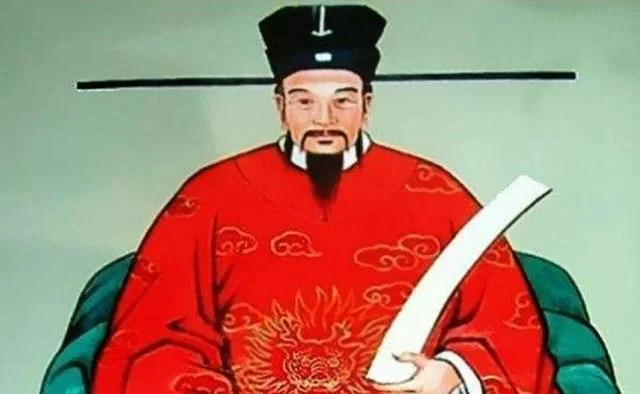
“丞相有副业”,这句看似调侃的话,实则精准地触碰到了古代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个极为核心且容易被混淆的概念:丞相与宰相的边界。当我们谈论蜀汉的擎天柱石诸葛亮时,这种混淆尤为明显。他究竟是丞相还是宰相?他的权力为何如此庞大,以至于“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根源上厘清丞相与宰相的权力来源及其本质区别,进而审视蜀汉政权这一独特的历史样本。
首先,我们必须破除一个常见的误区:丞相与宰相并非同一概念的不同称谓,它们在权力结构、法律地位和职能范围上存在本质差异。宰相,本质上是一个制度性的、职能性的概念,它是官僚体系的最高首长。自隋唐确立“三省六部制”后,宰相不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共同构成。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制度本身,决策需要经过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流程,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衡。宰相更像是一个大型企业的CEO联席会,他们的权力是程序化的、被制度分割的,旨在为皇权服务的同时,防止个人权力过度膨胀。
而丞相,则更多地体现为一个人格化的、授权性的职位。它的权力并非源于一套精密的制度设计,而是直接来自皇帝的托付与信任。在汉代,丞相是“百官之长”,总理全国行政,其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独立的府署和属官,理论上可以管理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军事、司法和财政。这种授权模式,使得丞相的权力边界极具弹性,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以及丞相本人的能力与威望。因此,当有人说“丞相有副业”时,他描述的正是丞相这种超越本职、囊括万象的权力形态。所谓“副业”,在旁人看来或许是军事、监察、地方行政,但在丞相的职权定义里,这些都可以是其“主业”的延伸,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是皇帝的全权委托,而非制度的分块赋权。
理解了这一根本区别,再来审视诸葛亮为什么是丞相不是宰相的问题,便豁然开朗。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授予诸葛亮的是“丞相”之职,并加“录尚书事、假节钺”。这一组合授权,是解开谜题的关键。“录尚书事”意味着诸葛亮可以总领尚书台,直接处理全国行政文书,掌握了政府的日常运作核心。“假节钺”则赋予了他在战时代表皇帝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的特权,甚至可以斩杀违抗军令的将领。此外,他还兼领益州牧,掌控了蜀汉唯一根据地的民政与财权。
这种集行政、军事、民政于一身的权力架构,正是丞相这一职位的极致体现。他不是在履行一个制度性“宰相”的分工协作职责,而是在行使皇帝授予的“总代理”权力。蜀汉建立之初,国力孱弱,内外交困,刘备需要的是一个能将整个国家机器拧成一股绳的绝对核心,而不是一个需要处处制衡、议而不决的官僚领袖。因此,他选择了制度上更为集权的“丞相”模式,并赋予诸葛亮超越常规的授权。诸葛亮的“副业”——亲自校对簿书、处罚二十军棍以上的士兵、管理后勤粮草——并非不务正业,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作为蜀汉“总管家”的本职工作。他不是在“兼职”,而是在履行一个被高度浓缩的、无所不包的“丞相”职责。他的人格魅力、绝对忠诚和无与伦比的才能,使他完美地适配了这一角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丞相”形象最光辉的典范。
那么,蜀汉的丞相有几位?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意蕴深远的问题。从严格的名号上看,蜀汉政权官方任命的“丞相”只有两位:诸葛亮和他的继任者蒋琬。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权力实质,就会发现答案远不止于此。诸葛亮是蜀汉唯一一位拥有并实际行使了完整丞相权力的执政者。他去世后,蜀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蒋琬作为诸葛亮的指定继承人,起初被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后来又加封“大司马”,但终其一生,他并未被授予“丞相”的头衔。费祎继任后,官职是“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样,他也未曾被称为“丞相”。这并非是刘禅或蜀汉群臣的疏忽,而是一种刻意的制度调整。诸葛亮时代的丞相权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应对生存危机而形成的“战时体制”,其高度集权的特征对于国家长远发展而言潜藏着风险。蒋琬和费祎虽然继承了“录尚书事”这一核心权力,执掌朝政,但他们的官职从“丞相”变成了“大司马”和“大将军”,这标志着蜀汉的权力结构开始从“丞相模式”向一种更为分散的、更接近后世“宰相”集体执政的雏形演变。他们不再像诸葛亮那样一人独揽军政大权,而是与其他重臣(如董允)分工合作,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因此,可以说,蜀汉真正的“丞相”,只有诸葛亮一位。蒋琬和费祎更像是拥有宰相实权的执政大臣,而非拥有丞相名号与全权的“大家长”。
从蜀汉丞相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即在皇权与相权之间永不停歇的博弈与调整。从汉初丞相的权倾朝野,到汉武帝设内朝削弱外朝,再到隋唐三省六部的权力分割,直至明太祖朱元璋彻底废除丞相制度,皇权不断强化,相权则从独立的权力中心逐渐演变为皇权的执行工具。蜀汉政权,仿佛是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微缩实验场。在立国之初的危局中,它选择了回归汉初的“强丞相”模式以凝聚国力;当政权稳固后,又自然而然地开始探索权力制衡的道路,尽管这种探索因国祚短暂而未能完全成型。
回过头来看,“丞相有副业”这句话,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它点明了丞相这一职位的本质:一个被皇帝全权委托、其权力边界模糊、包罗万象的国家管理者。诸葛亮以其一生的实践,完美诠释了这一点,他的“副业”清单,恰恰勾勒出蜀汉国家权力的全貌。而他之后,蜀汉不再设立拥有同等权力的“丞相”,则反映了一个政治体从生存高压期向常态治理期转变时,对权力结构的理性反思。丞相与宰相的一字之差,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和权力逻辑,而蜀汉这段短暂而璀璨的历史,为我们理解这一差异,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