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不赞同兼职取酬,朝过夕改君子赞同,但今人古人谁更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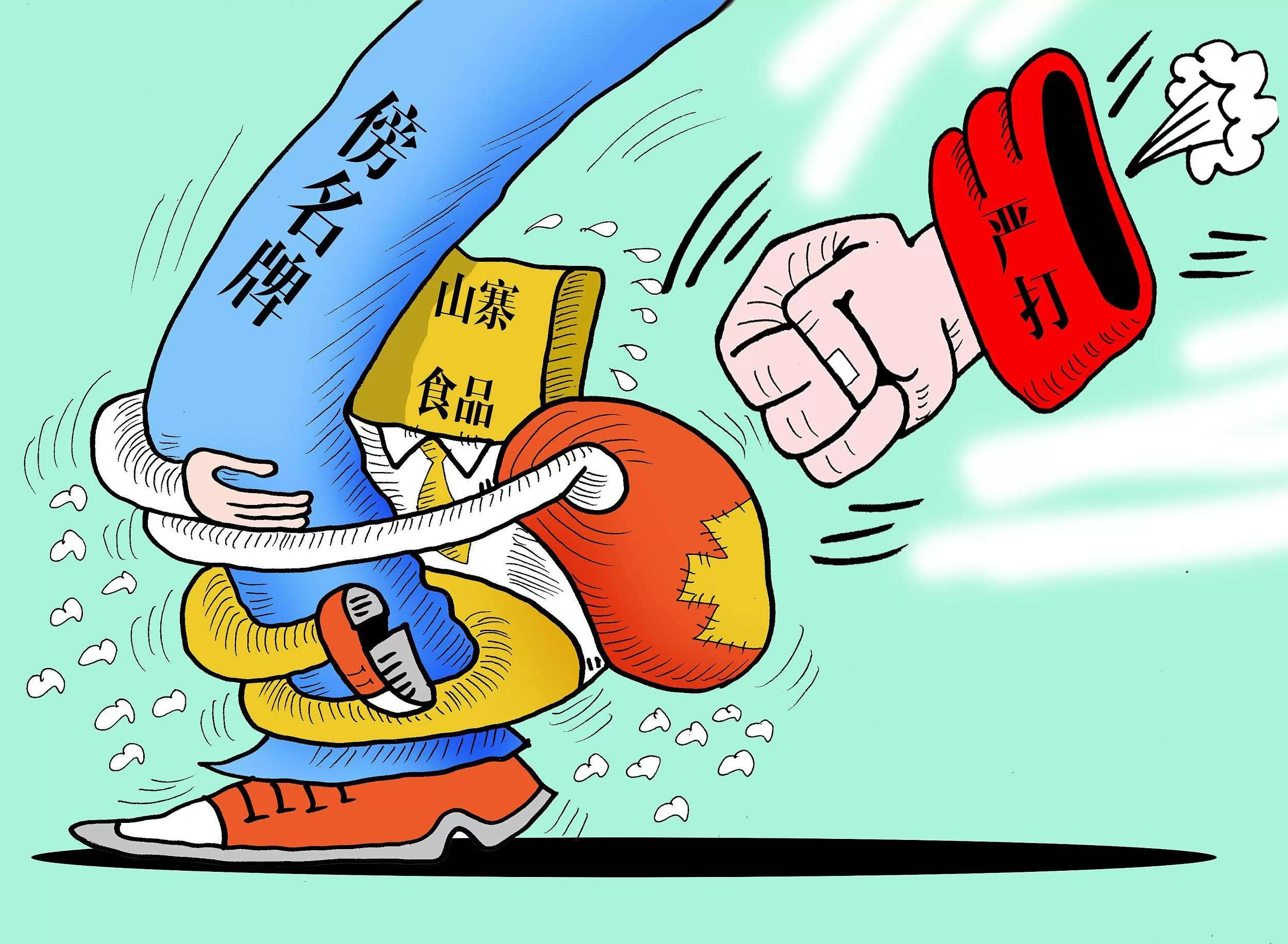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兼职取酬”或称“搞副业”,已然不是一个新话题。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个体生存的焦虑、对未来的盘算,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然而,当我们拨开这层现代经济行为的外衣,触及其内核时,会惊奇地发现,它所引发的争议,竟与千百年前古人的某种价值观念形成了深刻而有趣的呼应。那句“君子不器”,言犹在耳,似乎正是对现代人“身兼数职”最古老的批判。于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不赞同兼职取酬,是一种坚守,还是一种束缚?若说“君子不器”的古训在今日已显陈腐,那么,古人今人,究竟谁更具穿越时空的智慧?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古代如何看待兼职取酬”这一问题的深层逻辑。在以“士农工商”为社会结构基石的传统中国,职业分工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伦理秩序。“士”读圣贤书,求治国平天下之道;“农”勤于稼穑,固国之根本;“工”精于一技,传世之匠心;“商”流通有无,利民之所需。这种结构要求每个阶层、每个个体都安其本分,专其业。一个读书人若沉迷于经商,会被讥为“志趣不高”;一个农民若弃田而去,则被视为“不务正业”。这种看似僵化的分工,其背后蕴含着一种对“精一”与“忠诚”的极致追求。专注,是通往卓越的唯一路径。 一个铁匠,若心心念念的是田里的收成,他的锤艺便无法精进;一个朝廷命官,若私下经营产业以谋取私利,他对君王的忠诚、对百姓的责任便必然会打了折扣。因此,古代对兼职取酬的不赞同,根植于对“德”与“能”的双重考量。它并非简单地反对多劳多得,而是担忧一种核心价值的稀释——当一个人的精力与心思被多方利益所牵扯,他对主业那份纯粹的奉献精神便很容易被磨损,最终可能导致“样样通,样样松”的平庸,甚至诱发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腐败。这便是“君子不器与兼职的矛盾”在古代语境下的具体显现。“君子”不应当是一件有特定功用的“器”,更不应为了几件不同功用的“器”而割裂自己统一的人格与追求。
然而,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现代职业观与古代价值观冲突”在“兼职”这一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单一职业的“铁饭碗”早已被打破,企业裁员、行业变迁的风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在这样的背景下,兼职或副业,从一种“非分之想”演变为许多人的“理性选择”乃至“生存必需”。它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更被赋予了多元的意义:它可以是对主业技能的延伸与深化,一个程序员利用业余时间为中小企业开发小程序;可以是对个人兴趣的探索与变现,一个文案工作者在周末经营自己的美食公众号;也可以是应对未知风险的战略储备,一个普通上班族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理财、做代购,为自己的家庭构筑一道经济防火墙。从这个角度看,古人所倡导的“精一”,在现代社会似乎需要被重新诠释。那种将个人与某个固定职业、某个单一场域进行捆绑的观念,已然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朝过夕改”在这里,并非是君子之变节,而恰恰是君子之智慧。 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与发展趋势(“势”),固守成规反而是一种愚钝。懂得审时度势,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以多元化的技能组合来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自洽且积极的处世哲学。今人的智慧,体现在其对复杂性的理解和灵活性的追求上。
那么,副业是否违背职业道德?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它触及了这场古今智慧交锋的核心。古人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即便是在现代,副业带来的负面效应依然客观存在。例如,利用公司资源和信息做自己的项目,这显然违背了契约精神与职业伦理;因副业过度消耗精力,导致主业表现下滑,这不仅是对雇主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身职业信誉的损耗;更有甚者,主业与副业存在直接竞争关系,这就构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些行为,恰恰印证了古代先贤的远见——当一个人的“器”用过多,其核心的“道”就容易迷失。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怎么做”。古人的智慧在于其警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多元发展的同时,必须守住一条底线,那就是“正”与“诚”。今人的智慧则在于其方法论,我们有能力、也必须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建立起一套新的规则与自律,来驾驭这种多元性。
真正的智慧,或许并非在“古人”与“今人”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汲取双方的精髓,实现一种融合与超越。我们可以将古人的“君子不器”理解为一种“价值内核”的不可分割性,而非“技能形态”的单一性。君子可以掌握多种技艺,但驱动他运用这些技艺的,应当是统一的、高尚的价值观。他的内核是“诚”,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他的内核是“敬”,是无论对哪份事业都保有的敬业精神;他的内核是“仁”,是其创造的价值最终是否有利于社群的健康发展。基于这样一个稳定而强大的内核,再去探索职业的多种可能性,便不再是“逐利”的分裂,而是“体道”的统一。具体而言,一个现代“君子”在考虑兼职取酬时,应当遵循几条内在准则:其一,主业为本。副业是锦上添花,不应本末倒置,更不能以损害主业的根基为代价。其二,价值创造。副业最好是个人能力的延伸或兴趣的升华,它应当能带来知识、技能或社会价值的增量,而不仅仅是金钱的堆砌。其三,边界清晰。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厘清主副业的资源、时间和利益边界,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与滥用。如此,副业便不再是腐蚀君子之德的“旁门左道”,而成了丰满君子人格的广阔天地。
说到底,古人的智慧在于其深刻的洞察力,看透了人性中因追逐外物而可能导致的内在失序。今人的智慧则在于其强大的建构力,能够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里,为自己设计更复杂、更具韧性的生存结构。将二者对立,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惰性。我们不必苛责古人未能预见今日的职业生态,也无需因拥有了现代的灵活性而轻视那些古老的训诫。真正的智慧,是手持古人的戒尺,去丈量现代的路径。 它要求我们,在每一次“兼职取酬”的选择面前,都能反躬自省:我这样做,是在拓宽我的人生,还是在稀释我的核心?我的技能在多元,但我的人生价值是否依旧统一?当一个人能自信地给出肯定的答案时,他便超越了“古人今人谁更智”的二元诘问,活出了属于他自己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智慧。